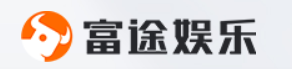专访苏童:在花草枯荣间,读懂生存比死亡更值得书写
日期:2025-07-25 18:59:44 / 人气:68

这些年,除了写作,苏童将最多心思倾注在他的花园里。这个肤色黝黑、精神矍铄的中年 “园丁”,每天在院子里摆弄花草,从调整娇嫩花草的摆放位置到为它们浇水翻土,乐此不疲。满园花草的枯荣交替,那些精心照料却突然枯萎的遗憾,与被弃于角落却寒冬后发芽生长的惊喜,都让他深深感受到:花草的世界,正映照着他所理解的人生 —— 有死亡,有重生,有枯荣。而这种对生命的体悟,也悄然改变着他的写作:如今的他愈发坚信,生存比死亡更值得书写。
从 “香椿树街” 到 “咸水塘”:写作地理的拓展与深化
苏童新作《好天气》的问世,距离其上一部长篇小说《黄雀记》已过去十二年。这部最初计划超过百万字、名为《咸水塘史》的作品,最终被他 “腰斩” 至五十万字,并赋予新名。书中的地理标签 “咸水塘”,虽看似与他此前创作中标志性的 “香椿树街” 不同,实则是其地理坐标的自然延伸 ——“往北挪了几公里就到了‘咸水塘’”。
创作过程中,苏童本无意回到香椿树街,却被故事里 “母亲” 的脚步牵引,“被香椿树街‘打了个伏击’”。这种创作中的 “不可抗力”,让 “咸水塘” 成为香椿树街的拓展与延续。与聚焦市民生活的香椿树街不同,“咸水塘” 的故事属于郊区,承载着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交汇碰撞的猛烈变化。一方水塘,五色天空,切割着生死与城乡,延续了苏童标志性的梦幻笔触,却也注入了对时代变迁更深刻的观察。
对于新作,苏童坦言收到的多是赞美,他笑称这让自己 “沉浸在一种并不真实的快乐的情绪当中”,但也不排斥批评意见。这种从容的态度,恰如他对写作地理的处理 —— 既扎根于熟悉的生活场域,又不断拓展边界,在延续中寻求突破。
生存比死亡更值得书写:创作理念的静悄悄的变化
读过苏童早期作品的人,常会被其中幽森阴郁的氛围、与死亡相关的故事所触动。年少时的写作中,死亡似乎是故事 “相对容易的出口”,笔下人物的死亡来得轻易。而如今,这种情况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。
“中年之后,我笔下‘没有一个人物可以随随便便死去’。” 苏童如此描述自己创作心境的转变。在他看来,随着年岁增长,生存的意义愈发凸显,成为更值得深入描写的主题。这种转变并非刻意为之,而是源于对生命更深刻的体悟 —— 在花草的枯荣中,在岁月的流逝里,他愈发感受到生存的韧性与力量。
早年写作中,死亡或许能带来强烈的戏剧冲突,但现在的苏童更关注生命在困境中的坚守与延续。《好天气》中,人物的命运交织于时代变迁的洪流,他们的挣扎、坚守与成长,成为书写的重心。这种从 “死亡出口” 到 “生存赞歌” 的转变,标志着苏童创作的成熟与深化。
园艺与写作:在花草世界照见人生
苏童与园艺的结缘,始于买下带院子的房子。从最初院子的 “一塌糊涂”,到亲手种下第一束花,再到照料满园花草,他笑称自己是 “被自己诱惑着” 成为了园丁。每天在花园里忙碌一个下午,施肥、移盆、翻土,这些看似琐碎的劳作,对他而言并非休闲,而是日常,是 “对生命负责” 的体现。
花草给予苏童的,远不止视觉的愉悦。它们的枯荣交替,那些突如其来的枯萎与意外的繁盛,都让他对世界有了更直观的认知。“花草这个世界其实在映照着我所设想的整个世界,这个世界的枯荣、死亡,和它的重生。” 这种观察与体悟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写作。
他将对花草生命的珍视,投射到对笔下人物的态度上;从花草生长的韧性中,汲取描写生存力量的灵感。园艺与写作,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件事,在苏童这里实现了精神上的贯通 —— 都关乎生命,关乎责任,关乎对世界的感知与表达。
文字的温度与结构的技术:对小说本质的思考
在苏童看来,中长篇小说必然有结构,结构也无疑是一种技术,但 “所有的技术都是没有温度的,而小说的温度是由文字散发的”。读者被小说打动,往往不是因为结构的精巧,而是被某个细节、某段文字所传递的情感与气息所感染。
《好天气》中,许多读者喜欢 “鬼凳” 这一意象 —— 奔跑的凳子,这与结构无关,却充满了文字的力量。苏童认为,读者感受到的是文字融合后超越感官的气息,这种气息才是小说真正的力量所在。技术结构可以完美科学,却无法产生这种直击人心的力量。
这种对文字与结构关系的理解,体现了苏童对小说本质的深刻把握。他不刻意追求炫技式的结构设计,而是将重心放在文字的打磨与情感的倾注上,让小说的温度自然流淌。
时代变迁中的写作:从 “神隐” 到面对碎片时代
十二年的创作周期里,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,这给苏童的写作带来了挑战 ——2016 年写下的人物,到 2021、2022 年再次出现时,他甚至会忘记名字。面对这种时间跨度带来的困难,苏童选择在时间上做一个了断,将故事聚焦到自己更有信心的 90 年代,书写郊区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消失,为那个时代的郊区唱一首挽歌。
“我认为这部小说,还是比较准确地呈现了郊区是如何一点一点消失的。” 这种对时代变迁的敏感捕捉,源于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。而身处短视频时代,苏童的身份也不再仅仅是作家。录制读书综艺《我在岛屿读书》时,他最初有些抵触和不适应,如今却已习惯 “经营自己的碎片”。
“我们都活在巨大的碎片里。” 苏童如此描述这个时代。八十年代,作家躲在文字背后,依靠模糊的照片维系着神秘感;而现在,神秘感不复存在,作家不得不走到台前,成为被公众注视的具体形象。他坦言,这种变化让作家与公众的关系发生了改变,读者会将文字与作家的具体形象关联,但没有作家能完全匹配读者的完美想象,对此作家必须坦然面对。
文学不死:在小众中坚守价值
面对非虚构兴起、科技发展带来的冲击,关于文学式微的讨论不绝于耳。苏童却显得从容淡定。他认为虚构类小说、诗歌等本就是小众的,市场的低迷或狭窄都属正常。“小说无用,音乐无用,美术也无用,但它们依然存在,且不会消亡。”
在他看来,科技并非文学的敌人,ChatGPT 等人工智能写出来的是人们已看见的东西,而作家的意义在于写出 “还没有被看见的东西”。这种对文学独特价值的坚信,让他在时代浪潮中保持着清醒与坚守。
对于电影等艺术形式的所谓 “式微”,苏童也持相似观点:“好电影还是有人看,不可能没人看。” 他反对匆忙得出 “某门艺术已死” 的结论,认为这些艺术形式只是可能不被某些人喜欢,并非真正 “病了”。这种理性的态度,体现了他对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 —— 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大众的追捧,而在于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。
结语:在花草与文字间,书写生存的力量
从摆弄花草的园丁到专注写作的作家,苏童在两种身份间找到了平衡与共鸣。花草的枯荣让他体悟生存的意义,写作的深耕让他传递生命的力量。《好天气》的问世,是他十二年创作心血的结晶,也是他对生存价值的一次集中表达。
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,在文学面临诸多挑战的当下,苏童以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写作的初心 —— 关注生存,倾注真情,在熟悉的土地上不断探索,在时代变迁中保持敏感与思考。正如他在花园中照料花草般,他也在文字的世界里,精心呵护着每一个人物,每一段故事,让生存的美好与韧性在字里行间绽放。这或许就是他想告诉我们的:在生与死的选择中,生存永远值得被书写、被赞美。
作者:富途娱乐
新闻资讯 News
- 排名第一与决赛缺席:国乒失利中...12-15
- 从 “不敢花” 到 “主动花”:全...12-15
- 160 万亿储蓄 “躺平”:谁在阻止...12-15
- 领免费鸡蛋引发厨房火灾:俞女士...12-1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