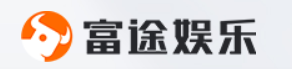我离开了 “原生公司”,却没能走出创伤
日期:2025-08-05 18:00:46 / 人气:57

“听到钉钉提示音就心跳加速”“看到节日慰问品会想起被羞辱的加班”“在新公司依旧不敢反驳上司”…… 这些看似偶然的情绪波动,实则是 “原生公司创伤” 的隐秘回响。它不是心理学术语,却精准描绘了许多人走出第一家公司后,仍被过去职场阴影笼罩的困境 —— 那些在职业生涯早期被刻入身体的恐惧、顺从与自我怀疑,即便换了工作,依旧如影随形。
离职后,创伤仍在身体里醒着
王珂离开前司一年零四个月时,在家门口的打印店被一声 “叮咚” 击溃。那是钉钉的新消息提示音,和他在前司被流程反复折磨、被财务刁难的记忆瞬间绑定。胃猛地抽紧,委屈和疲惫翻涌而上,仿佛又回到了为打印海报自掏腰包的下午 —— 那时他不明白,为什么一个简单的申请会被三方询价规则死死卡住,直到同事垫钱才了事。
更隐秘的触发点藏在节日的慰问品里。前司规定 “入职不满一年无资格领取”,他曾尴尬地收回伸出的手,转头却被领导叫去搬别人的慰问品,从大院到六楼,礼盒的重量压在胳膊上,也压成了记忆里的褶皱。两年后在新公司,看着同事排队领福利,他突然定在原地,那个被拒绝的下午再次漫过来,让他动弹不得。
Tina 的创伤藏在手抖里。作为校招进入前司的产品经理,她曾期待在这里快速成长,却每天活在 “这点事都处理不好” 的训斥里。最崩溃的那次例会,领导突然质问她 “请假为什么不找好 backup,请假了也需要参会”,冰冷的语气让她会后对着朋友泣不成声。后来,向领导汇报时手抖成了条件反射,哪怕跳槽后,梦里仍会重现被训斥的场景,惊醒后只剩心悸。
夏米的创伤则是 “被孤立” 的瞬间复刻。入职第五个月,她经历了领导的冷暴力:订奶茶唯独落下她,会议上暗示同事 “别理她”,她发言时全场低头看手机。那段时间,她焦虑到吃不下饭、呕吐、失眠,甚至停经。离职四年换了几份工作,可只要领导稍显冷淡,或在公开场合对别人热情唯独忽略她,那种窒息的不安就会瞬间将她拉回那个办公室 —— 旁人谈笑风生,她像个透明人。
这些创伤从不是单一事件,而是一系列持续的负面遭遇在身体里刻下的 “自动反应程序”。就像王珂听到钉钉声的生理紧绷,Tina 汇报时不受控制的手抖,夏米面对冷落时的瞬间恐慌,它们比记忆更顽固,成了隐形的枷锁。
我们是如何一步步 “被驯化” 的
“既然那么痛苦,为什么不立刻走?” 这是每个经历原生公司创伤的人最常被问的问题。可现实里的 “留下”,往往是权衡之下的无奈,甚至是被温水煮青蛙式的驯化。
王珂的留下始于现实的掣肘。父亲病重让他从成都辞职返乡,在广西很难找到对口的编辑运营岗,好不容易入职当地知名媒体公司,却被安排做行政和催债 —— 学习三方询价、登记固定资产,甚至被客户短信电话轮番催款。他申请换岗,领导春节前答应协调,年后却反悔。“跳槽太频繁简历不好看” 的念头,加上请假困难无法 “骑驴找马”,让他只能告诉自己 “起码撑到一年”。
夏米则是被 “温情话术” 套牢的。面试时,几位女性领导温和地介绍公司案例,说记得每位员工生日,会送限量周边,打造 “像家一样的团队”。这些细节让她卸下防备,哪怕入职后发现部门气氛压抑、加班成常态,仍像温水里的青蛙,忽略了环境的危险。领导当众说 “是个人在我手底下培养两个月,都能成为资深文案”,她忍着 —— 毕竟自己大学时就是专栏作者,想靠项目成果证明自己。直到被孤立到身体垮掉,才惊觉早已深陷。
Tina 的驯化则源于 “学生思维” 的延续。刚毕业的她把领导当 “老师”,把职场当 “考场”,在意每一句评价。领导在评审会上质问她保留跨部门模块的决策,而这项决策本就是领导拍板的,可她第一反应是自责。后来她发现,领导的批评常是情绪发泄,比如质疑某项设计,她连夜协调评估确认无需修改,对方却只说 “我只是想批评你”。久而久之,她不再辨对错,只用 “好好好” 应付,直到年底项目表彰名单里唯独漏掉她 —— 连外围同事都被感谢,她才明白这是 “系统性忽视”。
这些留下的理由背后,藏着职场新人的共同困境:现实选择少,离开成本高;对 “第一份工作” 有滤镜,期待 “再坚持一下就会好”;甚至将学生时代的 “听话”“求认可” 带入职场,把权力压迫内化为 “自己不够好”。就像被慢慢收紧的绳索,直到窒息才发现,早已失去挣脱的力气。
不是矫情,是权力结构下的集体困境
“是不是我太矫情了?”Tina 崩溃时不止一次这样问自己,直到在 “原生公司创伤” 的帖子下看到上百条相似留言 ——“听到领导咳嗽就紧张”“看到未读消息红点就窒息”“不敢拒绝加班,怕被说不敬业”。那一刻她明白,这不是个体脆弱,而是群体性的 “创伤症状群”。
天津师范大学王行坤副教授的分析戳中了本质:第一份工作是个体首次直面现实权力结构的场域。它延续了家庭和学校的顺从逻辑,又将人扔进更复杂的权力游戏里。企业为了驯服员工,会用 “温情话术” 包装压迫,用 “人格化管理” 模糊边界,让你在 “是不是我不够好” 的自我怀疑中,接受被支配的状态。
这种支配藏在细节里:夏米遭遇的 “不请你喝奶茶”“不接你话茬”,是用冷暴力制造孤立;Tina 经历的 “无理由批评”,是用情绪发泄强化权威;王珂面对的 “流程卡脖子”,是用规则制造无力感。它们不写在制度里,却比制度更有效 —— 让你觉得反抗不合时宜,把压迫当成 “正常”。
更残酷的是结构性焦虑的加持。经济下行期,优质岗位稀缺,“稳定工作” 成了奢侈品。应届生为了 “履历好看”,哪怕痛苦也硬撑;职场新人怕 “跳槽频繁” 影响未来,只能在创伤中隐忍。就像王珂说的 “起码撑到一年”,夏米想的 “积累作品再走”,本质上都是在稀缺性下的无奈妥协。
从 “被创伤” 到 “能疗愈”:既要自我救赎,也需制度托底
离开不是终点,但疗愈可以从离开开始。
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段锦矿的建议直指核心:先学会 “外归因”。王珂后来意识到,钉钉声本身不可怕,是前司的流程折磨让他有了条件反射;Tina 慢慢分清,领导的情绪发泄不是她的错;夏米开始明白,被孤立可能是领导的问题,而非自己 “不值得被喜欢”。“别闭环于自己的猜想,主动和同事求证”,这是打破自我否定的第一步。
建立边界同样重要。Tina 在新公司练习 “向上管理”:开会前和领导确认议程,被批评时当场澄清事实,开车时不接工作电话。她发现,领导并没有因此不满,反而更尊重她的专业度。夏米则学会了 “物理隔离”,前司领导的微信设成 “不提醒”,看到类似的冷暴力苗头就及时沟通,“我感觉被冷落了,是有什么误会吗?”
更幸运的是,好的职场环境本身就是疗愈场。Tina 在新公司遇到了 “讨论问题而非甩锅” 的团队,领导会说 “你觉得这样改怎么样”,而非直接训斥。她慢慢重建了自信:“原来我没有那么糟糕,还是有人愿意看见我的价值。”
但个体疗愈不该是唯一的出路。王行坤的提醒振聋发聩:“不能只靠自己舔伤口,更需要制度变革。” 透明的评价机制、落实的劳动法、员工组织化程度的提高,才能从根源上减少创伤的发生。就像王珂期待的 “流程公平”,Tina 渴望的 “认可透明”,夏米需要的 “反冷暴力规范”,这些都不该只靠运气获得。
那些在原生公司留下的伤疤,或许会永远带着淡淡的印记,但它们可以不再疼痛。当我们学会分辨 “不是我的错”,建立起保护自己的边界,同时一起呼唤更公平的职场生态,创伤就会从 “枷锁” 变成 “铠甲”—— 提醒我们曾怎样挣扎,更让我们懂得如何珍惜尊重与自由。
毕竟,职场不该是创伤的温床,而应是让人成长的土壤。
作者:富途娱乐
新闻资讯 News
- 排名第一与决赛缺席:国乒失利中...12-15
- 从 “不敢花” 到 “主动花”:全...12-15
- 160 万亿储蓄 “躺平”:谁在阻止...12-15
- 领免费鸡蛋引发厨房火灾:俞女士...12-15